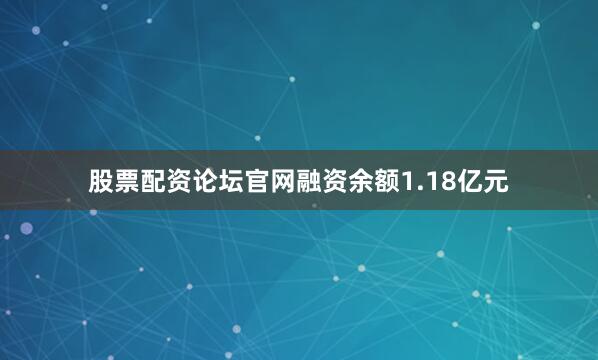【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当地时间7月5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报告和选举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直指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简称“秘密报告”),认定其“存在严重错误”,旨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
这份在冷战巅峰时期引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核弹”,在近七十年后,其冲击波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再次回荡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内外。
如今,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持续胶着、俄罗斯社会面临空前外部压力与内部整合挑战的背景下,俄共重拾这份尘封近七十年的报告,对其进行“历史性的修正”,其意义绝非简单的“翻案”或学术争论。
这枚“旧炸弹”的新回响所指向的,既是历史深处被扭曲的真相,更是当下硝烟弥漫的现实战场。它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究竟错在何处?它给苏联、国际共运以及中苏关系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如何科学评价?而此刻俄共的决议,又承载着怎样的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
展开剩余81%斯大林
三、重估“钢铁时代”——斯大林的客观历史坐标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我们评价这样一位深刻塑造了20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巨人,既不能如赫鲁晓夫般陷入歇斯底里的全盘否定深渊,也不应滑向无视错误的盲目崇拜泥潭。唯有将其置于其所处的、极端严峻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与“显微镜”,才能勾勒出符合真实历史的轮廓。而中国共产党客观、辩证、历史的评价原则——斯大林的一生“功过并存,功大于过”,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穿越历史迷雾的“指南针”。
(一)历史唯物主义定位:在特定环境中锻造的“钢铁”
评价斯大林,必须首先理解他所面对的历史舞台——一个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诞生的、经济文化异常落后、濒临崩溃的新生苏维埃政权(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实质性掌舵);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包围、封锁,时刻面临扼杀危机的环境(法西斯威胁由远及近直至战争爆发);一个肩负着史无前例使命——在落后国家率先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实验。正是这残酷的条件,塑造了斯大林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被称为“钢铁时代”的特质:高度集中、强调国家动员力、生存法则优先于民生、战时色彩浓厚。
在如此恶劣的历史背景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这构成了其历史坐标中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
1.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奠基人:锻造强国脊梁
面对社会主义事业“建成还是灭亡”的生死考验,斯大林力排众议,于1928年推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这一战略在短短十余年间创造了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1937年工业总产值较1913年增长7倍)。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钢铁、煤炭、石油、电力产量爆炸式增长(例如,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至1940年的1500万吨;发电量从1928年的50亿度增至1940年的480亿度)。建成世界领先的军事工业,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奠定了关键物质基础,如著名的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伊尔-2强击机等划时代武器系统的研发与量产能力,直接源于此时期的工业布局。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使苏联具备了在未来卫国战争中绝境求生的物质实力,更铸就了支撑其日后数十年作为超级大国的国本脊梁。没有斯大林的铁腕工业化,“社会主义生存”都成问题,遑论其后的世界地位。
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全国工业化
2. 卫国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力挽狂澜的英雄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发动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入侵,代号“巴巴罗萨行动”。战争初期,苏军遭受惨重损失,大片国土沦丧,国家危在旦夕。
但斯大林在极端困境下迅速承担起最高统帅的重任。其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决定性战役中展现的战略决心、资源调配与协调能力,是苏军最终由溃败转入相持直至转入反攻的关键(尽管具体战役指挥常由总参谋部如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执行,但斯大林作为最终决策者居核心地位)。
他领导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时总动员之一,将整个国家的工业(乌拉尔、西伯利亚后方基地)、农业、人力转化为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其坚韧不屈的意志成为激励全国军民的精神象征。
在付出了2700万军民(最新史学研究表明此数字已趋近共识)巨大牺牲的代价后,苏军在斯大林领导下不仅将法西斯侵略者完全驱逐出国土,更解放了中东欧,攻克柏林,最终粉碎了纳粹德国。
斯大林作为战时最高统帅和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人类文明免于法西斯奴役作出了不可磨灭、决定性的贡献。这一功勋超越了任何党派意识形态之争,是世界历史公认的伟大成就。
3. 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与巩固者:面对“狼群”的不倒盾牌
苏联建立之初及斯大林时期,面临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外部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间谍渗透、外交孤立;内部有旧势力的反抗(如富农)、反革命叛乱、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激烈挑战、乌克兰等地的民族主义分离活动,以及党内复杂尖锐的权力斗争。
在这种严峻环境下,斯大林以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苏维埃政权在狂风暴雨中的生存。其领导的肃反运动虽犯有严重扩大化的致命错误,但不可否认也在客观上挫败了部分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内外阴谋。他领导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后来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成为凝聚国力、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尽管其长远弊端巨大)。应对战时叛变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俄罗斯解放军”)和战后初期分离主义倾向,他采取了严厉措施(如对车臣等民族的强制迁徙,虽为严重错误,但体现其维护国家统一核心的逻辑)。
评价此点,必须承认其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下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基础,使其得以延续数十年,并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可观察的样板,尽管这个样板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无此盾牌保障,则苏维埃政权可能早已夭折。
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与推动者:世界革命的支点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作为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共运无可争议的核心。斯大林本人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与实践者,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象征性旗帜。在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虽受其严密控制)在指导、组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和战后初期)。
苏联在二战后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决定性支持(政治、军事),极大扩展了社会主义阵营。其对新中国的建立与初期建设也提供了关键援助(如“156项”工业援建项目)。对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越南、朝鲜在战后初期的抗法抗美斗争),苏联也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在自身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尽管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兄弟党和国家的政策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控制过甚等问题,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堡垒和大后方地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球反帝反殖斗争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发布于:上海市股票配资门户论坛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广州配资公司北青体育在官博晒出了球员抵达大连下榻酒店的视频
- 下一篇:没有了